2日上午10時許,車從湖北進入陜西白河縣境。
撒滿山嶺的陽光,在蒼翠的山林與火紅的楓葉上跳躍。
奔騰的漢江,穿梭于崇山峻嶺;輪下的公路,與漢江纏綿同行;越山過澗的襄渝鐵路,夾江向前伸展。江不舍路,路不離江,構成陜南道中奇特的風景。
“哎呀,這里堵車了!”司機發出一聲驚呼。
放眼望去,前面是一條車的長龍。重噸位卡車、客運車、越野車與小轎車,雜陳路中,不見盡頭。
從車里下來,我們在車與車之間穿行。掛有“麻虎”路牌的地段,一片泥石流占去公路半邊。20多個民工,正在突擊疏通。
“這路怎樣了?”我們問一個陜西大貨車司機。
“還能怎樣?”陜西司機吃驚地瞪圓眼睛,“前幾天下過雨。雨季里,這路十天就有兩個五
天堵。”
“那怎么辦?”“天要下雨,山要滑坡。人力怎能抗拒?!”
無奈,只好等待。誰知,這一等竟過去近兩個小時。
越過險段,路面變得復雜起來。我們乘坐的越野吉普,不時駛入滿是泥漿的地段,像一艘激流中的船,搖搖晃晃地艱難行進。
倚江開山筑成的公路,高出江面七八米,或十多米。從山坡上滑落的土石,往往墜入江中,把江面染成片片土黃。
沿蜀河與漢江交匯處前行,公路裂開100多米長的縫隙。車行其上,人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要不了多久,這些裂開的路面,終不免滑落漢江。
車出旬陽縣城10多公里,又一處泥石流鋪滿路面。我們的車再次被困住,4個多小時后才得以脫身。
夜幕早已拉下,好不容易到達安康,司機掐指一算:“從白河堵車到此,不到兩百公里路程,竟走了上十個小時。”
翌日一路行來,316國道始終與漢江如影隨行。多處被滑坡堵塞的路面,令我們目光不忍相接。
到達漢水源頭漢中,《陜西日報》駐漢中記者站站長楊建平,問起旅途情況,我們如實相告。
“這就是漢江兩岸的交通特點。”楊建平略有所思,不無沉重地說,“古往今來,秦巴山區,就是這樣被嚴峻的自然環境逼著倚江修路。”楊建平告訴我們,蜀道之始的古褒斜棧道,就是一個明證。
褒斜“棧道千里,通于蜀漢”。《戰國策·秦策》和《史記》,對此皆有記述。酈道元《水經注》稱,“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,門穿山通道六丈有余。”千古流傳的摩崖石刻“石門漢魏十三品”,對古人依江開山筑路,也有著明確的記載。褒斜棧道,這條我國歷史上持續3000多年的交通要道,就是沿著漢江主要支流褒河開山延伸,從漢中越秦嶺而達關中。
往事千年,滄桑巨變。置身褒斜棧道遺址,我們思緒萬千:在南水北調中線上游水源區,如何看待倚江筑路現象?
漢中市水土保持工作站站長余海明認為,漢江流經漢中城固、洋縣、西鄉等地,兩岸近百公里均屬風化花崗巖地帶,雖有青山掩蓋,但山石易于流失。縱橫交錯于漢江流域的公路干線與支線,如同為花崗巖風化流失開了一道道口子。
踏訪中,我們到過漢中、安康一處處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的小流域,都在公路沿線。漢中、安康的同志說,之所以這樣做,一個重要的目標,就是為了減少水土流失引發的公路坍塌,減少山石泥沙進入漢江干流與支流。漢中、安康人十分珍惜水資源,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鄂西北與陜南山水相連,同處南水北調水源區,同處壁立千仞的秦巴山區,鄂西北境內一些地方,也倚漢江走向筑路,也有滑坡山石墜落江中。倚江筑路,這是現實的選擇。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苛求這種選擇。然而,倚江筑路引起的地質變化、山體滑坡、淤塞江河,卻令人憂慮。顯然,實施南水北調中線工程,漢江上游水源區的道路如何建、怎樣管,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緊迫問題。
友情提醒 |
本信息真實性未經中國工程機械信息網證實,僅供您參考。未經許可,請勿轉載。已經本網授權使用的,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,并注明“來源:中國工程機械信息網”。 |
特別注意 |
本網部分文章轉載自其它媒體,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行業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在本網論壇上發表言論者,文責自負,本網有權在網站內轉載或引用,論壇的言論不代表本網觀點。本網所提供的信息,如需使用,請與原作者聯系,版權歸原作者所有。如果涉及版權需要同本網聯系的,請在15日內進行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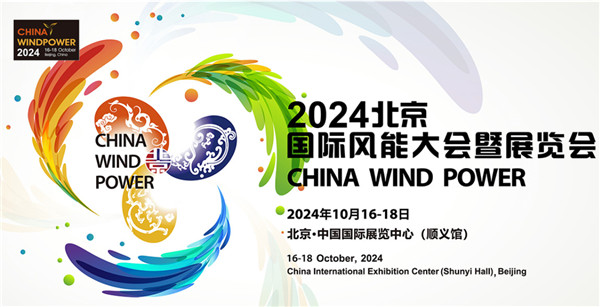 2024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..
2024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.. 2023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..
2023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..